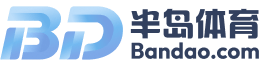BOB半岛赖特·米尔斯是一位走心的社会学学者。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方法论上的精微阐述。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对当代治学困境做出了可谓深入骨髓的剖析:方法和数据上做精做细只会产生平庸;好的社会学作品,或者好的社会学治学之道,在于从自身困惑与公共话语的重合面上挖掘可探讨的主题,把解决自己个人困惑的路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路径相统一,并以具有人文素养的语言把这一过程通过学术平台进行呈现。中国儒家思想强调“修齐治平”,把自身修为与天下平定相结合,在政治生活中同时改善个人和维护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而言,把米尔斯说成是美国版儒家知识分子,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恰当BOB半岛。
米尔斯所辩护的伟大理念是自由与理性。这两大理念也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传统德性追求。从德性追求的角度而言,米尔斯似乎承接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主义哲学传统。密尔曾在《功利主义》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快乐的猪”。他的中心问题是:是当一只快乐的猪好,还是当一个痛苦的人好?密尔的答案是后者,因为一只快乐的猪无论多快乐,它能也仅能知道自己的快乐;相反,一个痛苦的人既能知道自己的痛苦,也能理解猪的快乐。理性、知识和智慧带给人更高级的快乐。痛苦的觉知永远胜于快乐的无知。
似乎是为了响应密尔,米尔斯在《白领》中提出了“快乐的机器人”这一个概念,认为现代人的自由被技术化的工作和生活挤压,逐渐失去了自我反思能力。白领们疲于奔命地工作,并非是理性(reason)的结果,而是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结果:白领们无意识地、不得不去适应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以及职业市场对他们的要求。工作之外,时间和精力被消耗在“找乐子”上。在“快乐的机器人”的生活里,理性的自我反思无法占有一席之地。所谓思考变成了没有理性的合理化。在米尔斯看来,美国社会是一个理性难以扎根的“美丽新世界”。
米尔斯认为知识分子是理性火种的守护者。但他也悲观地看到,无理性的合理化主义——这种在美国白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思想现象——早已在美国的社会学界蔓延开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前六章里,米尔斯对学界存在的几种合理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它们分别是:宏大命题、抽象经验主义、各种实用倾向、科层制气质和各种科学哲学。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各种的学术工作方法。所谓的可以如此理解:工作者通过满足形式,向资源分配者表彰自身努力以求得某种资源回报;它的特点在于把精力放在满足形式化要求,而非解决实际问题上。《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米尔斯临终前对学术,甚至可以是对本身,发起的最后一次冲锋。
米尔斯在书中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宏大理论过分概念化、理论化,“把用语之争取代事实之辩”。书写宏大理论者喜好用晦涩、拗口的词句掩盖其对历史事实了解的贫乏。宏大理论者是自恋的。他不关注事实,而只在自己建构的概念里打转。米尔斯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反例。后者为了阐述“社会秩序建立在共同接受的价值”这一简单命题,用了洋洋洒洒的555页(第43页)。米尔斯认为,虽然这也算是一点洞见,但根本是一种对假设概念的形式化讨论,既没有历史证据作为支撑,也无法对实际研究案例进行观照,更无助于辨识社会现象。而且,其辞藻过分复杂,不利于理解。术语本来是为了方便思考而打造的工具。但帕森斯的术语建造了知识高墙,拒读者于千里之外。帕森斯用理论和修辞回避了经验研究,塑造了自己身为社会学家的假象,展现出了对自己概念的盲目崇拜。
如果说宏大理论者呈现出了一副脱离实际的自恋狂倾向的话,那么抽象经验主义者则失去自我,被合理化主义完全规训,彻底放弃了反思能力。与宏大理论相反,抽象经验主义是高度技术化的。它的主要操作方式是:获取统计数据,把这组数据与另一种变量相关联,然后在方法论的辩护下形成结论。在米尔斯的时代,这种操作方法很快演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工业化流程:“在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多少标准化的统计分析,‘拿到数据’,‘跑一下数据’,通常由那些半熟练的分析员来做,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之事。然后以为社会学家,甚至是一组社会学家就会被雇佣,‘线页)。这进而引发了研究问题与数据本末倒置的问题。
根据米尔斯的观察,在实际操作中,抽象经验主义者先通过数据分析形成结论性观点,然后才围绕着观点安上那么几句文献综述和历史背景勾勒。社会学理论对抽象经验主义而言是一种包装程序,用于欺骗知识消费者。用米尔斯的话说:“这的确会误导局外人,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心实施,在经验上足以检验更为宽广的概念或假设”(第97页)。抽象经验主义者擅长于量产论文,是知识生产工厂的能工巧匠和先进分子。但他们不关心研究问题本身。如果说车间工人的身体被机床异化,那么抽象经验主义的思维则被方法论吞噬。
作为社会学家,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智识困境?米尔斯给出的了一个出奇地简单却又引人深思的回答:提出好的问题,并尝试回答它。社会学和科学不一样。好的社会学研究既不是靠演绎推理得到了的(像宏大理论那样),也不是靠归纳总结得来的(像抽象经验主义那样)。相反,只有在提出值得研究的、对人类经验有价值的问题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对之解答的情况下,社会学家才能打造出历久弥新的著作。
从这个角度而言,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研究绝对不是二战后那种高度技术化的美国模式,而是19世纪的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发展出来的经典模式,这种模式不拘泥于方法论,不从宏大概念出发演绎推理,而是把焦点放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上,并在行文中通过引述不同学者的争论,时刻与这个实质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第178页)。这些问题直指他们当时所处社会环境下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那些东西,比如资本主义的产生和阶级不平等。马克思没有大数据,韦伯恐怕也不讲究什么方法论。他们能成为经典,不在于他们的回答,而更多在于他们提出了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构成了人们思考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
对于当代人来说,什么是值得研究的好问题?这并没有方法论可言。在米尔斯看来,好问题的发现是非常个人化、主观化的。要发现好的问题,必须努力寻找个人困惑与社会议题的交汇点,让这个问题成为连动个人与社会对话的齿轮。研究者要弄清楚“它们蕴含的价值和面临的明显威胁”(第180页)。对如何治学而言,米尔斯的论点意味着至少以下几点。第一,学者必须寻找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学术工作变成一项能同时解答人困惑和社会问题的事业。第二,学术不是一个技术活儿。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心理基础;也就是说,学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关注自己的心理和思维状况,否则他将因无所困惑而无法发现问题。第三,学者也不能仅仅在反思中作茧自缚。他要把自身的困惑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解决。他必须承认,人不是孤岛,不是单独的存在,他的心理状况是整个社会和历史时空作用下的产物。改变个人心理意味着要改变社会,反之亦然。
可见,学术工作做得是否富有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之外的滋养。好的学者总是关注他所能感受到最迫切需要解答的疑问,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这些疑问构成了像火焰般的心理驱动力,为他的研究提供能量。他很容易从他生命经验里获得启迪他的材料和灵感,尽管把这些经验导向学术工作并非他刻意所为,更不是他生活的目的。他左右逢源,经验自然地流淌在他敏锐智觉的周遭。
这提醒我们必须摒弃那种把学术工作看成工作,把学术与生活机械分割的业绩主义思维。当今中国,学术工作很容易成为一个攒文章数量和积分的大型电子游戏。玩得好的人当然也有,但似乎大多数人都是内卷化下被压迫的学术工匠(特别是所谓青椒)。对于他们来说(包括我),观察生活并形成学术问题似乎跟自己的生命没有关系。学术问题的提出成了职业要求,一项必须做的形式化工作环节。对于那些没有拔群智商作为支撑的学者来说(比如我),他们的工作会很痛苦了。
最好的情况下,学术是一项磨人而高雅的爱好;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不赚钱的谋生手段;最差的情况下,是对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负荷。他专注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彝族的萨满教仪式以及美国六十年代的对华外交政策,但这些学术书写只能偶尔让局外人对他的才华点头称赞,却无助于使他生活得更睿智。它们或许能被转化成论文,变成他事业的助力。但那建立在牺牲睡眠、饮食乃至人际关系上。它们或许能为他带来专注、简单的满足感,但却造成了日常生活上的割裂:他变得孤单,难以成为更大社会团体的一份子。他被局限在了他狭窄的思想圈子里。
如果一个学者要成为米尔斯笔下的优秀学者,那么,他需要的就不是仅仅改变作息、每天坚持写作半小时或抽空精读《国富论》。他需要更本质的改变:重构自我,把自我看作并体验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里的产物;他要通过反省自我来观察社会,并与社会对话来调适自我。他需要摒弃“一切与我无关”的虚无主义,以及“我的主观能决定一切”的全能自恋。这么做需要颠覆性的想象力。或许连那也是不够的。用今天话说,做好学术,他需要走心。至少这样解读,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米尔斯把他的书命名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