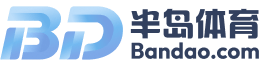BOB半岛《跨国交织下的帝国命运》,吴翎君著,联经出版公司,2024年2月版,452页
近二十年来,几乎与欧美学界同步,全球史研究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专门研究团队,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四年后的2008年又创办了《全球史评论》的研究集刊BOB半岛,投稿应接不暇。接下来相继成立“全球研究院”或“全球研究中心”的国内学术机构,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以“跨国史/全球史”命名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这些年来少说也有上百场,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千篇,专著业已超过三十部。今年四月,云南出版社推出由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教授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该书由二十三位研究者联手撰写,三卷本,一千六百多页,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与此同时,今年二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也出版了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吴翎君撰写的《跨国交织下的帝国命运》,全书八章,四百余页。比较而言,前述葛兆光教授主编的那部著作,属于“案例研究”,主要从战争、商品、宗教、气候、疾病等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讲述自远古以来“跨国史/全球史”的诸多历史演化BOB半岛。吴翎君教授的这本著作,以两次战争、自强运动、国际法和多样化的国际组织、清末立宪革命与商人及现代城市发展为经纬脉络,讲述了十九世纪中叶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融入世界的故事,属于总体性、全面性及概论性的“通史写作”,有更多可被关注、评论的话题性及争议性。毕竟,此前的“中国近代史”或可分为两类。一是“国族史观”,如蒋廷黻、陈恭禄、郭廷以、徐中约等人的著述,较多关注中西冲突、救亡图存。另一是“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如范文澜、李时岳、陈旭麓及近来由张海鹏等人主编的相关著述,多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重点讲述反抗/侵略、进步/落后。共同点都只是就中国而论中国,外部世界仅作为事件展开的背景,并没有特别呈现“跨国史/全球史”意义上的复杂、多元之联结与互动。
进而言之,作为中英文世界里的首部“全球史/跨国史”研究框架之下的“通史书写”,《跨国交织下的帝国命运》声称“中国化”(internalization)和“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不能被本质化或固定化,而应视为两个相互交错、不断游移和辩证的状态或坐标。前者是指在西方强力冲击之下,中国社会的自我更新和蜕变内化;后者是说中国历经磨砺,跌宕起伏、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在作者看来,晚清中国苦苦寻找在这两个坐标中的文明定位,并认为“不论自主或被迫加入国际大家庭,帝制中国的命运其主体性和执行仍是一种自我抉择”(17页)。就此来看,该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思想创新意义大致有三:
首先,在华西方是否拥有单方面的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之魔力;抑或还有在地碎片化意义上“混杂”(“hybridity”)的另一面?以往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之下,主流叙事通常会以二元对立的视角,认为在华西方与本土社会总是势不两立,非此及彼,并在两者的矛盾对立中无往不胜,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了西方霸权。本书则认为不论来自西方的技术、理念、人员、机构,乃至制度和语言等,如果要想在中国社会发挥作用,必须与在地及本土元素进行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沟通、谈判、协商和妥协。这也就是被许多学者称之为“扩散化”的举措和行动,外来(或在华西方)遂“与当地社会之间的互动催生出了新的文化范式、身分认同、社群组织,以及对政府治理的新挑战等等”(14-15页)。
其次,晚清统治在对外事务中是否总是冥顽不灵、顽固不化,抑或还有审时度势、力图补救的明智之举?在以往的主流叙事中,晚清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最不堪回首的耻辱年代,留下了太多关于统治和精英阶层“软弱无能”“”“保守固拒”“用人不当”等刻板印象。本书则认为晚清发生了许多涉外战争,精英们在讨论主战抑或主和的立场时,反帝的民族主义论述便是一再拉高主战的声量,并被美化为民族主义英雄;而主和则被视为软弱受辱的一方,甚至妖魔化,从而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牺牲和损失。毕竟,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深刻危机,晚清统治仍勉强持续五十年之久,可见并非那么的昏庸不堪,作者也就希望“回到当时人的行为、动机和结果来评价其历史定位”(421页)。
再次,造成大量无辜人民伤亡的,除列强入侵之外,是否还应注意兄弟阋墙、骨肉同胞间的相斗及相残?针对以往主流颇多肯定反叛起义,或不太反省频频爆发的血腥内战,本书则认为列强发动的战争,不论就持续时间、动员兵力、交战地点和规模而言,都不算大,也不是焦土性的侵略战争。相反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内战,清王朝和太平军激烈的交相残杀,“才造成数以百万的士兵和无辜人民的死伤悲剧“(12页)。再按照著名全球史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说法:各地战乱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在整个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如太平天国、捻军、西北和云南及引发的饥荒,死亡人数估计有三千万(《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上册,强朝晖、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42页)。
虽则,本书主旨在于“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黯黑史”,但不意味着作者无视或掩盖那些罪行。如谈及1850年代后,英美等列强希望以修约方式,打开中国大门而扩张经济利益,本书说为了急欲达成某些特定目标,列强愈来愈走向躁进的作为,显得极其荒谬,交涉过程也更为粗暴,遂发生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等一连串的疯狂举动”(72页)。再谈及1900年来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称众多俘虏被残暴虐待和无情枪杀,联军士兵再次打开圆明园等地的大门,大肆抢夺珍贵文物和皇家的珠宝器物。本书记有:“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入侵的一年前,这八个列强全都加入了1899年的《海牙公约》,明文禁止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战时抢夺和恣意杀戮。”(92页)
由此可见,本书重心不集中于“帝国主义侵略”,是希望用更多篇幅呈现我们自己的历史能动性(agency)。如随父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尼日利亚移民美国,现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哲学的塔伊沃(Olúfẹ́mi O. Táíwò)教授,于2020年出版的《反对去殖民化:认真对待非洲能动性》(Against Decolonisation: Taking African Agency Seriously)一书,反对不加区别地将“去殖民化”应用到文学、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医学等所有领域。在塔伊沃看来:来自欧洲的“现代性”(modernity)不应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混为一谈,更非“西方”“白人”或“殖民”所独有;非洲人民有意识地将之付诸实践,通过创造性地挪用、转换和综合,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在地及本土的历史能动性。
虽说上述两部著述,代表了中文世界里相关研究的最新趋向,但我们还需要针对当下时代的严峻挑战,对未来可能的学术发展再做一点反思。原因在于该研究深受1990年代那一波“全球化”的激励,看重历史上与之相应的人员、器物和文化的流动、循环和融通,较多讲述在此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并没有特别在意其中的暗潮汹涌BOB半岛、险象丛生。现实情况却是:一些新兴国家搭此波“全球化”的顺风车,虽实现了快速发展,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却造成了大范围的贫富悬殊、社会撕裂和环境灾难。再随着肆意鼓吹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民粹政治人物遂先已强势崛起,不久前消停的新冠肺炎又为此波“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俨然成为不可逆的时代主流。
与之相应,前不久那场致使七亿人染病,一千三百余万人死亡的世纪大瘟疫,我们曾经在惊扰中提心吊胆,惶恐度日,当下怎能不对以往一味称颂的研究倾向做些调整?2023年6月号的《美国历史评论》刊发了一组题为“关于跨国史”(On Transnational History)的论坛文章,论及此次疫情对研究研究产生的影响。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辛迪·尤因(Cindy Ewing)发表的文章,称研究者必须反思为何这场大瘟疫没有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或让我们意识到共同人性;反而让更多人退回到民族主义的激进形态,不断拉高了人们之间的怨怼、猜疑和仇恨(“Troubling the Global South in Global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 128,No.1,June 2023,pp.270-271)。
太阳底下本没有多少新鲜事,或可参照中国近代史上颇为相似的案例,是1910年冬爆发至1911年春结束的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其时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清铁路,及以大连为中心的“南满铁路”,分别由沙俄、日本控制,全面进入世界市场的出口经济,如大豆、煤炭、粮食等,汇集了大批来自山东、山西、直隶等地的华人劳工。还有盛产于俄属西伯利亚、蒙古、我国东北的旱獭皮毛,在欧洲市场上备受青睐,华工贪图丰厚收益而成了捕猎者。然旱獭却是鼠疫杆菌的携带者,将疫病传染给密切接触,且居住环境极差的捕猎者们,随即在四通八达的区域经济体系蔓延,并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自北向南迅速传播,外溢至京津、山东、汉口、浦口的六十五个县市,至翌年春季罹病死亡人数已超过六万。
作为对那时“全球化”影响更具包容性的反思,我们无法忽略在那个抗生素没有诞生的年代里,肺鼠疫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典型症状是突然出现头痛、发热、咳血、肺部大面积感染,重症者两三天后痛苦死亡。疫情爆发之后,哈尔滨、大连的日本、俄国殖民统治当局,随即采用了强制性暴力(unmitigated tyranny)检疫、防疫。如哈尔滨的沙俄殖民市政当局征用货车车厢当作隔离营,派遣武装士兵严加看管,擅自逃脱者格杀勿论。那时的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度,既没有必要的取暖设施,又无法提供充足的食物,时人说“不死于疫,必死于检疫、防疫”。殖民统治者则声辩道:文明的法则就是“寓仁术于暴行中者”,“杀少数以卫多数”(《敬告部派督派有防疫专责者》,《远东报》1911年1月4日,第1版)。
正如前不久的疫情肆虐,危机时刻的相扶与相助,伸出援手,最让人感激涕零,刻骨铭心。同样,上述那次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之时,地方社会、邻里之间彼此照应,共渡难关,最值得大书特书。如为应对当局搜寻病患及密切接触者的粗暴检疫,民众组织起来,在街头巷尾派出儿童哨兵,看到搜寻人员马上报警,病人及尸体就会迅速转移及藏匿起来。因为那些执法检疫人员,并非专业医护人士,看到脸黄体弱者,将其与周边之人强行送到隔离营;发现不明尸体,遂将房屋付之一炬,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太多烦扰。此外,商会、同乡会馆与当局反复谈判,经过不懈抗争,终获准成立自主隔离病院。虽与西医一样,他们也无法治愈患者,但至少可让濒临死亡之人,身边有亲人们的看护和照料,不至于在惊恐万分中悲惨离世。
由此回到本稿关于需要调整研究取向的话题,概括说来,我们似不能只看到流动、世界、光明的那一面,而也应适当注意不动、原乡、阴影的另一面。这样方可在对比和参照中,更好地展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善意、爱心与美德,以求更有效地应对眼前甚嚣尘上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之大退潮。毕竟,在那次东北疫情即将结束之时,清政府出资十万两白银,邀请三十四位来自英、美、日、俄、德、法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以及五位亲身参加过救治及防疫事务的中国学者,历时二十五天,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全面总结了此次检疫、防疫及治疗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会议的开幕式上,东三省总督锡良代读摄政王的贺电,称赞与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将推动人类事业的发展和为人类带来无穷福祉”(will advance the cause of humanity and bring infinite blessing to mankind)。这种将中国事务与人类命运紧密连接的理念,自然应成为当下我们相关书写调整的核心关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