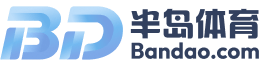BOB半岛古埃及人称自己的语言为“神的语言”,语言最先由创世之神使用。在《尼罗河畔的曙光:古埃及文明探源》一书中,作者考察了埃及文字起源的神话,梳理了古埃及文字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古埃及象形文字从诞生时起就更注重仪式性功能,其发明和使用不是出于记录账目或行政的需要,而是与宗教信仰和统治者的权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期“世界”栏目节选了本书第六章《书写与艺术的起源》第一、二节。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另拟。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一位名叫仓颉的圣人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而创造了文字。但古埃及人认为,他们的象形文字并非某位智者的发明创造,而是直接来自神。文字不是源于人类的智慧,而是神对人类的馈赠—智慧之神图特和他的妻子书写女神赛莎特(Seshat)创造了文字,并将使用文字的技能传授给人类。正因如此,图特神也被称为“神圣语言之主”。
古埃及人称自己的语言为“神的语言”,语言最先由创世之神使用。在孟菲斯神学体系中,孟菲斯地区的创造之神普塔用语言创造了世界。按现代语言学体系来划分,古埃及语言属于亚非语系(Afroasiatic),在欧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也称Hamito-Semitic,或Semito-Hamitic,即闪含语系。古埃及语同闪族语(Semitic)和伯伯尔语(Berber)的关系最近,与库希特语(Cushitic)和乍得语(Chadic)也有相关性。古埃及语言的使用涵盖了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300年,经历了从综合语(synthetic)到分析语(analytic)的转变。早期埃及语包括古埃及语和中埃及语。古埃及语主要在早王朝时期、古王国时期、第一中间期时使用。金字塔内部墓室墙壁上镌刻的《金字塔铭文》与官员陵墓中的铭文都是用古埃及语写成的。中埃及语又称古典埃及语,从中王国时期一直使用到第十八王朝末(公元前2000 年—前1300 年),在宗教领域,则一直沿用到埃及文明终结。从第十八王朝末到中世纪一直使用的古埃及语又称后期埃及语,具有分析语的特点。从第十八王朝末到公元前700年,后埃及语是使用最广的语言。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世俗体埃及语代替了后埃及语,主要用于文学作品与日常行政文书。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基督教化的埃及出现了科普特语,即以希腊字母拼写的古埃及语。
文字与书写是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宗教观念等文明要素相互碰撞的产物。古埃及象形文字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埃及国家的起源同步。从口语到书写的转变为古埃及社会带来了物质、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在经济层面,书写系统的完善使产品的分配与流通更加高效;在科学技术层面,文字的使用带来了天文、数学、建筑的发展;在宗教层面,原本以口头形式流传的经文和咒语经由书吏的记录与编辑成为系统的知识。象形文字不仅在社会经济与行政管理中具有实用性价值,也是宗教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埃及有关文字起源的神话反映了古埃及人对知识的认识。文字不仅仅用来记录语言,也用来记录知识。因此,文字是人类借由神的力量认识世界的工具,由神的语言书写的知识被称为“奥秘知识”。图特神了解和掌握这些奥秘知识,因此也被称为“奥秘知识之主”。
图特是书写和智慧之神,也是月亮之神与书吏的保护神。“图特神的追随者”是古埃及人对书吏的称号。在艺术作品中,图特神以朱鹭鸟或狒狒的形象出现。朱鹭鸟与图特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涅伽达时期。在前王朝时期的调色板上出现了朱鹭鸟栖息在旗标顶端的图案。图特神是众神的书吏,朱鹭鸟头人身的图特神常被刻画成手持芦苇笔和墨盒在纸草卷上书写的形象。在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插画中,死者由阿努比斯神带领来到冥界之神奥赛里斯面前,将心脏放在正义的天平上称量,负责记录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就是图特神。在《金字塔铭文》中,图特神帮助已故国王的灵魂升入天空中的神圣领域,向西方的众神宣告国王灵魂的到来。国王也需要借助图特神的翅膀才能飞到众神的世界。
古埃及的知识流传到了希腊世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关于古埃及文字起源的传说,他这样写道:
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城有一位古老而知名的神祇名为图特。名为白鹭的鸟是他神圣的象征。他发明了许多技艺—算数、计量、几何、天文、跳棋和骰子,但他最大的发明是文字。那时统治整个国家的国王是塔姆斯(Thamus),他住在上埃及的大城市里,希腊人称之为埃及的底比斯,称塔姆斯为阿蒙。图特向他展示自己的各种发明,希望其他埃及人也能够从中受益。图特一边一一列举,塔姆斯一边询问这些技艺的用处……当说到文字时,图特说:“这项发明可以使埃及人更聪明,增强他们的记忆力,是改善记忆和智慧的一剂良方。”那位国王答道:“多才多艺的图特,技艺的发明者并不总是能够恰当评价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于使用者而言究竟有什么用。现在,你作为文字的父亲,对你宠爱的孩子言过其实了。这种发明会在学习者的灵魂中播种下遗忘的种子,因为他们不会再使用他们的记忆力;他们将会依靠外在的书写符号,而不是靠自己去记住。所以,你发明的这剂良药不会帮助记忆,只能帮助回忆;你赋予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表象;他们道听途说了不少,却什么都没有学会;他们看起来全知全能,却基本上什么也不知晓;他们将成为令人生厌的人,炫耀虚假的智慧。
在这里,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话表达了对文字的消极态度。他认为,人们使用文字后将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反而依赖符号,最终导致创造性思想的丧失。然而,这并不是古埃及人的本意。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中,文字和书写的诞生与世界的诞生处于同一过程。换句话说,书写的发明是创世的一部分,是先于人而存在的宇宙真理。语言文字是神赋予世界具体形式的工具,被写下来的文字是神创造万物的标记。在世界诞生之前,图特神是“拉神之心”,或称“拉神的观念”。创世是通过神的语言实现的。因此,图特本身就是“创世魔法”,通过创造语言从而创造世界的一切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图特赞美诗》(The Hymn to Thoth)纸草文献中,描述了图特以文字和语言来创造世界的过程:
我是图特,我向你重复拉神的话,因为在这之前有人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图特,我掌握神圣的文字,这文字能将事物放在它们合适的位置。我为神奉献供品,我为受到保佑的死者奉献供品。我是图特,我将真理放入写给九神的文字中。从我口中出来的一切都将成为真实的存在,正如我就是拉神。我不会被任何力量从天空中和大地上驱逐出去,因为我知道天所隐蔽的事情,这些事情不会为地上之人所知,它们隐藏在原初之水中。我是天空的创造者,在山峦的起始之处。我用思考创造河流,我创造了湖泊,我带来了泛滥,我使农人得以生存。
孟菲斯的创世神话更加清楚地阐明了语言文字与创世的密切关系。这篇神话写在第二十五王朝的一块石碑上,即沙巴卡石碑(Shabaka Stone)。石碑铭文记载了创世之神普塔将自己头脑中的概念转变为客观存在,并通过语言创造世界的过程。普塔神先在心中设想,之后用言语使所想成为具体的存在—“普塔创造众神。普塔,众神之父,通过自己的心与舌创造九神。”铭文还提及荷鲁斯是普塔之心,图特是普塔神之舌。普塔作为创世神是隐藏的,荷鲁斯和图特作为普塔创世力量的载体是显现的。换言之,普塔通过思想和语言创造万物,心(荷鲁斯)思考后,舌(图特)将思考的成果显现出来:
伟大的普塔神通过心与舌给予众神生命。荷鲁斯以普塔的形象出现,图特以普塔的形象出现。心与舌在所有生灵内,人类、牲畜、爬行动物等一切生灵接受普塔心与舌的指令。
由此可见,在孟菲斯神学体系中,世界起源于观念和语言。将心中构思的表达出来,实体就出现了;通过语言说出事物的名字时,事物的形体也就存在了。“神圣之话语”是创世的核心。象形文字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是现实世界中某一个具体物件的图像,文字本身却是观念和思想的表达。可以说,文字符号是沟通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桥梁。神创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将观念中的世界变为现实世界的过程。因此,现实世界是观念的反映,而有具体形象的象形文字符号也是人们心中观念的反映。
名字是神创造世界的关键,古埃及人因此非常看重名字。他们认为,名字是实体在观念中的存在,只有叫出名字,事物才能存在。在神创造世界之前,宇宙处于一片混沌,当时被称作“没有任何事物的名字能被叫出之时”。古埃及君主在建筑物和雕像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防止自己的名字被人遗忘。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永远抹去他的名字,因为没有了名字,就意味着不再存在。新王国时期的“异端”法老埃赫那吞就是因为背弃阿蒙神信仰,转而崇拜唯一的太阳神阿吞,而遭遇了“灭名之灾”。他的名字被抹去,后世的王表从未记载过他,他的都城也埋没于黄沙之中。直到近代,埃及学家才通过考古发掘知道了这位“异端”法老的存在。在涅伽达文化时期的标牌上,最早出现的也是人名和地名。在一则关于太阳神拉的神话中,伊西斯女神知道了太阳神拉的名字,因此获得了拉神的力量。
由于象形文字来源于神,古埃及人认为文字和语言都具有神圣的力量,是魔法的载体。例如,表示“生命”的符号安柯会被制作成护身符供人们佩戴;表示“不朽”的符号杰德柱护身符则来自奥赛里斯的脊椎骨;表示蜣螂的象形文字符号是“出现、新生”之意,是死者通往冥界所必需的护身符。人们在书写象形文字时也需要遵从特定的规则,因为被书写下来的概念和事物会具有实体,魔法会依附于此产生作用。
古埃及人称魔法为赫卡(heka),是造物神在创造世界时使用的力量。赫卡也是魔法之神的名字。在创世神话中,魔法之神作为太阳神的巴而诞生,是最古老的神祇。魔法的使用需要咒语,若要将咒语记录下来,就需要同样具有魔力的文字。实际上,《金字塔铭文》就是古王国时期君主在丧葬仪式上使用的咒语。第一个把咒语刻在金字塔墓室墙壁上的是第五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乌纳斯。他在萨卡拉为自己修建了一座金字塔,并在金字塔内部的墙壁上刻上了丧葬仪式所使用的咒语。这些咒语可以保护死去的国王顺利升入天空,进入神圣领域。可以推测出,在咒语被刻在金字塔墓室的墙壁上之前,就已经以其他形式存在了,或是由祭司口口相传,或是记录在纸莎草上。然而,就算是具有神性的国王,也会对象形文字的魔力充满畏惧。金字塔墓室墙壁上很多人和动物的符号都是不完整的,甚至需要反向书写,如蛇和蝎子等危险动物的符号需要特别处理—或在身体上方画上一把尖刀,或是画成断为两截的样子。《金字塔铭文》是关于复活的咒语,而完整的动物和人的形象可能会因为魔法而复活,对墓主人造成伤害。可见在古埃及人的眼中,象形文字不仅仅是文字,作为文字符号虽然在词法和句法中有特殊的含义,但它仍然是具有生命力和魔力的具体图像。
正是因为象形文字具有这样的力量,掌管着文字的图特神也掌管着一切知识和咒语。关于“图特神之书”和奥秘知识的传说也一直流传甚广。中王国时期的文学故事《胡夫与魔法师》(Khufu and the Magician),讲述了古王国第四王朝时的国王胡夫觊觎图特神殿内隐藏的奥秘知识的故事。在托勒密时期的一部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图特神的魔法书。这部魔法书由图特神写成,记录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掌握了这些魔法就相当于掌握了宇宙的奥秘。在故事中,第一位得到这本魔法书的人是远古时代一位名叫纳奈弗尔卡普塔的王子。普塔神庙祭司告诉纳奈弗尔卡普塔,图特神的魔法书“被藏在科普特斯的湖心。湖心有一只铁盒,铁盒中有一只铜盒,铜盒中有一只凯特木盒,凯特木盒中有一只象牙乌木盒,象牙乌木盒中有一只银盒,银盒中有一只金盒,金盒中存放着图特的魔法书。铁盒外有蛇蝎及各类毒虫环绕,其中有一条无人能杀死的巨蛇。这些防备正是为了守卫图特神的魔法之书”。纳奈弗尔卡普塔前往科普特斯,杀死了神兽,偷来了魔法书。然而,图特神知道后,对他和他的妻子儿子施加了严厉的惩罚,令他们全家葬身水底,魔法书也随他一起封存在陵墓之中。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第四子哈姆瓦斯(Khaemweset)王子听说了图特神魔法书的下落,也想得到此书。他得到魔法书后,诵读了其中一条咒语,故事这样写道:
他震撼了天地、冥府、山河;他理解了空中的飞鸟、水中的游鱼和沙漠中的走兽的全部言语。他诵读了另一条咒语—他看到了天空九神伴随着太阳神普瑞(Pre)的身影;他看到了月亮升起,看到了群星本来的面目;他看到了水底的鱼,尽管那是水下圣肘尺的深处;他对着水面念诵咒语,水应声出现了原形。
在偷看了魔法书后,哈姆瓦斯王子也得到了神的惩戒,险些杀死自己的儿子。在明白了人类无法掌握神的魔法之后,王子归还了魔法书,将其封存在古墓中。
这样的情节设置表明,人类不能掌握神的魔法,奥秘知识必须被隐藏起来,神会惩罚将“奥秘知识”透露给世俗世界的人。“ 奥秘知识”具有巨大的威力,是关于宇宙、天地、冥府、星辰和大自然动物的最隐秘的知识,代表着宇宙的运行规律。“奥秘知识”的语言具有魔法属性,不仅对应着现实世界,也记录了宇宙万物中超乎人类理解的部分。
古埃及知识分子认为,宇宙、神、人之间有着不可僭越的次序。人虽然可以阅读神的文字,却不能掌握神的知识。从《胡夫与魔法师》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即便是强大的君主也不能触碰图特神的奥秘知识,如果僭越了人与神的界限,就得接受死亡的惩罚。古埃及有关文字起源的神话把文字的产生提升到了创世的高度,将文字的使用置于神圣的地位——文字并不只是语言的书写形式,更是观念的表达,是观念与现实世界产生联系的纽带,也是魔法和知识的载体。
一篇世俗体智慧文学《因森格纸草教谕》(Insinger Papryi )以师生问答的形式系统地展现了“奥秘知识”涵盖的内容:宇宙天地和世界万物、各种天文自然现象、社会生活中的魔法、法律、伦理道德、人的代际传承、等级系统和秩序。虽然文献中对奥秘知识的解释仍富有神秘主义色彩,但记载的知识本身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或神学观念,而是将神秘性赋予世界,是结合神圣与世俗的综合性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反映了古埃及祭司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思考,并将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同宇宙秩序融合在了一起。《教谕》这样写道:
太阳和月亮如何来往于天空?河流、太阳与风何时走,何时来?什么人使护身符和咒语成为治疗手段?这是神的隐秘工作,他让这些现象每天发生在大地上。神创造昼夜,万物在此中出现;神创造大地,生育万物,再将一切吞下,又再次创造;神通过命令之主的命令创造日、月、年;神通过天狼星的升起和落下创造夏天和冬天;神令食物出现在活人面前,那是田地的奇迹;神创造天空的星辰BOB半岛,大地上的人们才能了解星辰;神创造所有土地需要的甜水;神不知不觉间在胚胎中创造了呼吸;神令子宫接受,创造了生命,又用创造了肌肉和骨骼;神通过大地的震动创造了时代的变迁;神创造了睡眠来结束疲倦,创造了清醒来寻找食物;神创造治疗来结束疾病,创造美酒来结束痛苦;神创造梦,为迷失者指明方向;神创造生死折磨不虔诚的人;神给诚实之人带来财富,给虚假之人带来贫穷;神为愚蠢者创造了工作,为普通人创造了饭食;神创造了代际更迭而使人们存活下去;神对地上的人隐藏他们的命运……
正因为语言、书写与奥秘知识都与生命的诞生密切相关,知识因而也象征着生命的力量。古埃及人把图书馆称为“生命之屋”。在每一座神庙中,“生命之屋”犹如“中枢神经”,维持着神庙的运行和知识的传承,守护着以玛阿特为代表的宇宙秩序。在“生命之屋”中工作的书吏掌握着各种知识技能,他们拥有“ 神之书吏”“诵读祭司”“医生”“神的父亲”“皇室书吏”“图特神”等诸多头衔,并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官员辅助国王管理国家。在神庙之中设立的“生命之屋”既是保存各种典籍的地方,也是传授知识的学校。根据希腊化时 期的世俗体智慧文献《图特之书》(The Book of Thoth)的记载,在“生命之屋”中,祭司学习各类知识启蒙,成为图特神的书吏。祭司传授知识的过程也是死者复活仪式的隐喻,即亡灵进入冥界,经过夜晚复活再生的历程:
教育开始时,我的肢体……哦,我站立着,如同木乃伊。我已尝遍每一种药材,使我的身体干燥。哦,泡碱如同图特的文字符号在我的体内流淌……我已进入天空女神努特的循环……开始航行在知识的黑暗冥府之中。让我张开手抓住太阳神的船,愿我在他面前诵读“星之书”。我已看到狒狒正在惩戒巨蛇,他以强大的魔法将地面分裂。这里有四十二个巴。我已询问守门人关于太阳神拉的巴,他们守护着他。
在这一隐喻中,死者即学生。死者通过掌握知识而顺利通过冥府的十二道门。正如书中所言:
他开始掌握自己的眼、耳、心、舌、手、脚……你(指奥秘知识)已分开我的舌,你已为我开辟道路,你已给予我来去的方法,你已使我成熟,但仍旧年轻。
在后世文献的记载中也可以窥见古埃及祭司学习经典的情景。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Clemens of Alexandria)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古埃及祭司掌握的知识:
古埃及人追寻他们自己的哲学,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神圣的仪式中。首先是歌者,佩戴着表示音乐的符号。他需要学习《赫尔墨斯之书》(The book of Hermes )中的两本书,其一包括神的赞美诗,其二是国王生活的典章。在歌者之后是占星者。他手持时钟和笏板,这些都是占星的象征符号。他拥有赫尔墨斯的占星书,并将这四本书倒背如流。其中一本记载了肉眼可见的恒星的顺序,另外一本记录了日月合相与它们发光的时间,其余的都是记录关于星星的升起。之后出现的是神圣的书吏。他的头上戴着翅膀,手持书本和书写工具—芦苇笔和调色板。他必须掌握象形文字,知晓天文与地理、日月与五大行星的位置,还有关于埃及的描述,尼罗河的地图,关于祭司所用设施的描述,相关的神圣地点,以及度量衡和在神圣仪式中所需要的东西。之后是掌袍者,手持着正义的尺度和祭洒的圣杯。他装备着一切关于教育与献祭的知识。还有十本书记载了他们如何为神献上荣耀,包括了埃及式的礼拜,涉及牺牲、初熟果实、赞美术、祈祷、、节日庆典等等。最后是先知。他手中拿着水瓶,身后跟随着拿面包的人。他作为神庙的管理者要学习十本叫做“祭司文”的书,包括法律、神祇、以及全部祭司应掌握的知识。这是因为先知在埃及人中也是掌管收入分配的人。这样一共四十二本《赫尔墨斯之书》,其中三十六本包含了上述人员掌握的全部埃及哲学,其余六本是医学书,涉及人体的结构、疾病、治疗方法、药物、眼科、妇女病。这就是埃及人的习俗。
三十六和四十二这两个数字在古埃及文化中具有特殊含义。三十六代表 以十天为周期的三十六值星,象征着一年内天空星体的运行变化。四十二是古埃及国家统一的象征。自古以来,埃及的领土被划分为四十二个行政区域。在奥赛里斯神话中,赛特杀死奥赛里斯后,身体被分为四十二块,分散于埃及各个行省。因此,四十二这个数字就代表着奥赛里斯的身体被重新组合起来。埃及全国各地的祭司每年都会举行仪式,他们手持各自行省所保护的那部分奥赛里斯的身体汇集在一起,完成奥赛里斯的复活仪式。因此,四十二本《赫尔墨斯之书》象征着古埃及传承下来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承载着从神界到人间的一切智慧。
说到文字的起源,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文字。对埃及象形文字而言,究竟从何时开始,那些表示人物、动物、植物和日常器物的图像才可以被称为文字呢?有学者认为,当这些符号组合成一个序列,并且与口语有一定关联的时候,才能被称为文字。也有学者认为,文字是书写出来的语言,是人类彼此之间以可见符号为载体进行交流的系统。可以说,出现用于记录的符号,是文字产生的第一个步骤。
公元前4千纪后期,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尼罗河下游的埃及,人类第一次用符号记录信息,开始了书写的历史。在两河流域,文字最早产生于一个叫作乌鲁克的城邦国家。乌鲁克的先民用芦苇笔在一块压平了的潮湿泥版上刻出楔形线条,成为最早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主要用于书写日常文书和记录文档。
古埃及的情况与美索不达米亚有很大不同。在载体上,古埃及语并不写在泥版上,而是用墨水写在陶器上,或者刻在骨质或象牙小牌上,甚至刻在石头上。在纸莎草纸发明后,人们用芦苇笔蘸墨水直接写在纸上;在用途上,古埃及象形文字更多被发现于早期统治者和上层人物的墓葬中,以及神庙遗址中的祭祀用礼器上。因此,古埃及象形文字从诞生时起就更注重仪式性功能,其发明和使用不是出于记录账目或行政的需要,而是与宗教信仰和统治者的权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零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的大部分出土铭文都是名牌或简短的石刻铭文,内容以王名和地名为主。因此,对此阶段埃及语言的语法研究很难进行,对其解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此时的古代埃及语与王朝时代类似,也是由表音符号和表义符号组成的。第零王朝时,王名框已经十分常见。城镇的名字一般出现在表示围墙的符号内。此外还有表示数字的符号。与两河流域的计数方式不同,古埃及一直采用十进制计数法。
将符号组成序列的想法可能源自图画—将单个图画连在一起表达更为复杂和完整的意思,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在一起的图画就形成了一个序列。在前王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在画面上分行,用来表达事物的时间或空间序列。
从图画序列到文字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赋予符号读音。例如,纳尔迈王的名字用鲶鱼的符号加凿子的符号组成。鲶鱼和凿子并无关联,跟国王也没有什么联系。因此,这两个符号很可能是用来表示发音的。鲶鱼读作“nar”,而凿子读作“mer”,这位国王因此被称为纳尔迈。到了第一王朝,表音符号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顺序还不固定。在一枚象牙小牌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尼特-霍特普”这个名字,写于一位女性形象的头顶。左边的符号代表尼特女神;右边有三个符号排成一列,开头的符号代表“htp”三个辅音,是“满意”之意,第二个符号读作“p”,第三个符号读作“h”;在“尼特”与“霍特普”两个符号之间,还有一个较小的符号,读作“t”,表示在女神名字中“t”的音节。把单音符号写在多音符号之后再标明其读音的做法是后来象形文字书写的普遍规则。正因如此,现代学者才能推断出多音节符号的读音。在尼特-霍特普的时代,单词的拼写方式已经与后世通用的拼写规则无异了。
然而,在这之前,象形文字又是从何演变而来的呢?关于埃及文字起源的研究一般从古埃及文字的形成时间、文字与国家起源之间的关系、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两河流域古文明对埃及文字的影响等方面展开。早期研究者曾提出“三角洲起源”假说,即文字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最早的象形文字是用来记录另外一种语言的。当上埃及地区的涅伽达文化扩张到三角洲地区时,就吸纳了象形文字书写体系,用来记录自己的语言。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涅伽达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文化有着较为频繁的贸易联系,因此,古埃及人很可能是受到了乌鲁克的启发,而发明了文字。然而,这两种假说都缺乏足够的考古证据支持。首先,考古学家并没有在三角洲地区发现早期象形文字符号;其次,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无论是在字形上还是在用法上都相去甚远,二者的出现几乎同时发生。因此无法证明象形文字的发明受到了楔形文字的启发。
也有学者认为,涅伽达文化二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象形文字的雏形。当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被组合使用时,可以表达相对完整和复杂的意思,因此可以算作文字。皮特里在发掘涅伽达和胡(Hu)的时候,记录了当时发现的陶器符号。符号种类繁多,包括动物、船只、植物等,其中线形符号最为常见,有十字交叉线,之字形线,半圆形线,以及无法辨别具体形象的线条。在这些符号中,有一些在后来的象形文字中有迹可循,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法在文字中找到对应。在下埃及地区也发现了陶器刻画符号,但与上埃及地区的符号明显不同,年代上属于早王朝时期,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在希拉康波利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比较特别的陶器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属于前王朝时期,被刻在抛光陶片上。这些刻在陶器上的图画不是简单地表示某种动物或物体,而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一片陶片上,一条鱼和一只受伤的羚羊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组奇怪的动物形象。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组合可能是为了表达某种神话或宗教领域较为抽象的概念,而这种表达方式进而演化成文字。此外,某些组合如羚羊和鱼,也可能是由于发音的关系而写在一起作为某个人名的发音。符号组合的方式早在涅伽达文化一期末就已经出现。特定的组合可能是为了表达某种特别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早期陶器符号,特别是动物形状的符号,很有可能都是人的名字。前王朝时期很多国王的名字都取自动物,如著名的蝎王。因此,刻在陶器上的动物符号也有可能是普通人的名字,用来表示陶罐的所有权—把陶罐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并在上面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对丧葬品所有权的宣示意味着来世信仰的萌芽。在王朝时代,墓主人在随葬品上和陵墓中写下自己的名字,而名字在进入来世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葬品上所刻的名字,是将死者与随葬品联系起来的媒介。
然而,U-j 号墓中发现的文字还处于象形文字发展的初期阶段,对这些符号的解读有相当大的难度。除了动物与物品的符号,标牌上的一些线形图案可能也具有特别的含义。例如,圆环符号可能表示城市,而双线符号表示两片土地。U-j 号墓规模庞大,随葬品十分丰富,考古学家还在其中发现了一根权杖。由于在墓室内发现了多处蝎子符号,这些蝎子符号与表示地产的符号同时出现,因此判断这座陵墓可能是一座王陵,属于早期一位名为“蝎子”的君主,学者称其为蝎王一世。蝎王一世生活在涅伽达文化二期末年至三期初。当时的埃及还有其他的地方统治者,如希拉康波利斯第100 号墓与涅伽达地区T 形墓都是早期的王陵,由当地的统治者修建。
第零王朝以后,王名框出现了。写在王名框中的王名也开始广泛使用表音符号。王名框通常出现在大型陶罐上。这些陶罐中很可能装有早期国家收集的农作物,即谷物税收,还有一些可能是通过远途贸易交换来的异国产品。王名框与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意义在于表明王室对这一物品的所有权。陶罐上的铭文也越来越具体。古埃及早期国家可能已经开始使用文字来创建记录体系,从而能更好地管理农产品的贸易和分配。
到了第一王朝,象形文字书写系统已经基本成型,限定符号开始出现,后来使用的几乎所有的单辅音符号在当时都已经出现了。象形文字诞生之初,与圣书体象形文字一同出现的还有草书体。在纳尔迈调色板上,书写在王名框中纳尔迈的名字,就是典型的圣书体。而U-j 号墓的陶罐上以黑色墨水书写的“王名”,则是最早的草书体。因此,有学者认为,早期古埃及文字的两个主要功能是辅助行政和仪式性展示。传统观点认为,类似纳尔迈调色板这样的礼器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记录。近年来,学者更倾向认为这些礼器都是用于仪式性展示的。纳尔迈调色板上雕刻的国王打击敌人的场景仅具有仪式性的象征意义。在法老时期的浮雕和壁画中,这样的场景也往往只是王权和国王维护国家统一和平的象征,并不代表真实发生过的战役。因此,在这些礼器上的圣书体象形文字并非用于记录历史,而是用于传达与浮雕相同的信息—王权的神圣性与君主维护世间秩序的职责。
第一王朝早期,古埃及文明的开创者们在文字的使用上又有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的标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标牌上的画面不再仅限于一个或几个象形文字符号,而是由更复杂的文字和图画组成,在式样上也更为规整。画面一般分为若干行,图画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神龛、神圣的动物、图腾、宗教仪式场面等。一般而言,标签的内容可分为四类:年鉴标签,记录国王的名字和每年发生的大事;庆典标签,记录国王的名字和值得庆祝的大事;简短的年鉴标签,只记录国王的名字;简单标签,仅写有物品或地产的名称。
表示“年”的象形文字符号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这里的“年”并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自然年,而是以国王统治为划分依据的纪年法,即某王统治时期发生了某事件(通常是宗教仪式)的那一年,如“国王登举行赛德节的那一年”。纪年的出现表明早期国家形成了相应的记事体系,也说明国家的行政与祭祀活动都围绕着君主进行。
纳尔迈的陵墓中出土了一枚左下角残损的标牌。这枚标签雕刻精细,内容丰富,记载了一次纳尔迈王征服3000名利比亚人的军事活动。在标牌的右边写有纳尔迈的王名框。在标签的左上角,纳尔迈的名字被拟人化处理,以手拿着权杖打击敌人的形象呈现。敌人跪倒在地,头上长出三棵纸莎草。根据左侧的铭文显示,敌人的身份是利比亚人。在拟人化的纳尔迈名字之后是站在旗标上展翅飞翔的荷鲁斯之鹰。
另外两枚从早期王陵中出土的标签也记录了类似的军事行动。在阿哈的标签上,他的名字被写在带有荷鲁斯神的王名框内。在另一边,阿哈的象形文字符号也经过了拟人化处理,刻画成了手持权杖打击敌人的形象。标签上的铭文写道:“荷鲁斯阿哈打败努比亚人,伊缪特的诞生。”在登的标牌上,国王身穿礼服,身后装饰有兽尾,身前的敌人跪地求饶,而登则高举权杖作打击状。在登的王名框之前还有豺狼神的旗标,旁边的铭文可读作“第一次打击东部的敌人”。标签上的记录无疑带有神话色彩,将国王的事迹与宗教神话相结合,以节日仪式的模式来表述历史。
在萨卡拉一位高官墓葬中发现的一枚标牌上有十分复杂的构图和文字。在标牌的中间,登的名字被写在王名框内,左边是王室掌印官赫玛卡(Hemaka)的名字。在标牌的最右边写有表示“年”的符号。在“年”的左边是登举行赛德节的场景。身穿长袍、头戴象征上下埃及双冠的登端坐在神龛中。而在神龛之前,国王身着短袍,进行赛德节的跑步仪式。这枚标牌很可能是这一年的大事记,记载了“国王举行赛德节之年”发生的事情。
在同一时期位于北萨卡拉的另一位高官的墓葬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相似的标牌。这些标牌都是以表示年的符号为开头,包括了王名、官员的头衔和名字,以及陶罐所盛之物的名称等文字。比起U-j 号墓和阿哈统治时期的标牌,这些标牌上的内容更为复杂。首先,政治事件和纪年的结合,不仅体现了历法的发展,更体现了历法与政治的关联;其次,国家行政人员身处政治框架之内,象形文字也为官员所用,成为记录国家行政、经济和政治宗教仪式的工具。也就是说,古埃及文字虽然与国王的丧葬仪式和王室权威的展现密切相关,但在古埃及国家建立之后,文字又被应用于日常的行政管理和国家政治事件的记录中。
到了第二王朝,随着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私人陵墓中出现了供奉祭文。供奉祭文是古埃及墓室铭文中最核心的部分。祭文以固定的格式开头,即“君主所赐之供奉”;其后是奥赛里斯与其他神祇的名字和头衔;随后写出供奉清单,即一系列献给死者的供品的名称和数量,如“一千罐啤酒、一千条面包、一千头牛”等等。供奉祭文并不是陈述式的,而是将一系列短语和词汇固定,形成特定的表达句式。这种高度程式化的书写模式也证明了古埃及文字在诞生之初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语言。程式化的宗教仪式文书是古埃及高级文化的代表。这种语言和文字相分离的现象一直贯穿埃及文明的始终。供奉祭文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了埃及后期。与供奉祭文相结合的是表现死者坐在供桌之前接受供品的浮雕和壁画。与文字一样,古埃及的刻画艺术也是高度程式化的,并非人物的写实描绘,而是对人物形象的理想表达。
到了第二王朝末期,书写模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书写逐渐规范,符号的数量减少,单词的拼写也更为标准。此时的铭文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短语、清单、头衔或标题,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叙述性文本。在佩尔伊布森的一枚封印上有这样的句子:“奈布特万物之封印:奈布特之神为他的儿子统一了两片土地,上下埃及之王佩尔伊布森。”到了第三王朝初乔赛尔王统治时期,神庙墙壁上的铭文已经与后世无异了。
与两河流域和古代中国不同,古代埃及文字似乎是在第一王朝国家诞生之时迅速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埃及文字的诞生与政治密不可分。新诞生的国家在政治上尚不稳定,统治阶层需要将统治合法化,而对文字的使用正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除了政治上的作用,文字对于王室而言还有经济上的价值。在埃及统一和国家形成的进程中,统治阶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而文字的诞生可以有效地记录经济活动,方便国家对资源进行控制和调配。
对于一个正在快速演化成国家的社会而言,行政、书写和象征艺术是社会管理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书写作为关键要素之一,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组织形式。书写的发明、形式和用途在塑造不同的社会模式和国家体制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象形文字的使用使得国家必须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以培养出一批可以为行政管理体系所用的书吏阶层。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逐步形成,书写和艺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反过来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早期国家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新生国家对文字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行政管理,宗教崇拜和艺术表现。象形文字和图形的组合常常出现在各种标牌上,用于传递包括年代和事件在内的复杂信息。文字也是统治阶层的专属工具,如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陶罐上的封泥,都是用来表示这些物品是归统治阶层专属的。在统治阶层的墓葬礼器上,常常用文字标明特别的人物和地点,以向世人展示国王统治的合法性,如登基仪式、赛德节、军事胜利的场景等等。在这些场合中,统治者以全新的形象出现,代表着古埃及王权制度的确立。
在国家建立之初,社会意识形态需要被重新定义。传统的文化习俗通过精英阶层得以保留传承,而精英阶层也需要创造新的传统来适应阶层化的社会。在国家出现之后,文明内部各要素需要在新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之下重组。在这些要素中,神明与亡灵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构建社会记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由基本结构组成,包括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以及以非亲缘关系作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如经济集团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结构都遵循共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这种同一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规范,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中心,就是构建古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的形成是一个逐渐走向制度化的过程,人们接受社会秩序再创造新的秩序。文字的使用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
把国王的名字镌刻在其雕像的底座上,或在他的浮雕形象旁边,象征着雕像与浮雕表现的人物形象具有了国王的身份,从而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将国王的名字、他的统治年限与在任时的重大事件书写下来,就构成了最古老的“历史”和“年鉴”。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年鉴”写成于第五王朝,相对完整的帕勒莫石碑残片上刻有从第一王朝到第五王朝的王名及每位国王在位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年鉴看似是对王名和大事的历史记录,但其作用却不止于此。年鉴是刻在石碑上的,而石碑能够长久保存,主要在墓葬仪式中用于展示。在记录的形式上,年鉴不是记叙体的,而是以表格的形式来进行记录:石碑第一行镌刻的是神话中君主的名字,名字之下是表示君主的限定符号;第二行镌刻的是君主在位期间发生的事件,事件的记录以年为单位,而表示年的符号又成了每一栏的分割线;在事件一栏下方,还有每年尼罗河水位的记录。
文字符号形象及其空间排布形式都会对记录的内容产生影响。表示君主的象形文字符号刻画了君主的形象,其排列的次序代表了王位的传承;表示“年”的符号成了分割线,不仅代表时间,也区分了各个事件,以空间排布表达时间与历史的进程。如帕勒莫石碑上的文字已经完全脱离了对语言的记录,其排布形式是为了在石碑上展示王位的延续性与国王的伟大功绩而精心设计的。这也是掌握书写技能的知识阶层构建新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治理人间的国王代表人间的秩序,而时间的流逝则代表宇宙的秩序。年鉴通过书写的形式将这两者进行了结合,向世人展示了王权与自然秩序的统一。而石碑作为这一展示的载体,其永久不腐的特点让文字的宗教作用得以完美发挥。
综上所述,对古埃及人而言,书写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记录语言。书写系统是文明的一部分,书写这一行为(把文字刻在石碑、神庙或墓室的墙壁上)只是短暂的过程,其结果——具有展示作用的文字——则脱离了书写本身,成为纪念性建筑物的一部分。正如建筑物可以改建和增建,其上的铭文也可以修改和增补。通过对铭文的修改和增补,建筑物或雕像被赋予新的历史含义。
第二节希腊罗马与阿拉伯人笔下的埃及世界 ...... 18第三节古埃及文明的重现与埃及学的诞生和发展 ...... 28
第二章远古的足迹第一节古埃及文明诞生的自然地理环境 ...... 49第二节石器时代的埃及 ...... 64
第三章古埃及国家的诞生第一节涅伽达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 78第二节涅伽达文化的扩张 ...... 89第三节早期埃及国家的政治图景 ...... 103
第四章早期国家的发展成形第一节早王朝时期的埃及国家 ...... 122第二节金字塔时代的国家结构 ...... 133第三节官僚系统的发展 ...... 152第四节早期古埃及国家的对外交往与远程贸易 ...... 163
第五章早期国家的宗教观念第一节古埃及宗教的开端 ...... 175第二节太阳神崇拜的起源与发展 ...... 194第三节丧葬信仰与奥赛里斯崇拜的起源 ...... 210
第六章书写与艺术的起源第一节埃及文字起源的神线第二节古埃及文字的起源与演变 ...... 242第三节古埃及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