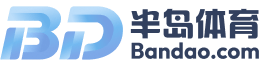BOB半岛作者:雷黎明(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文房”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文献,《梁书·江革传》载:“此段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这里的文房指官府掌管文书之处。至唐,文房被用来泛指书房,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文房长遣闭,经肆未曾铺。”宋代以后,文房逐渐成为传统汉字书写工具和载体,即笔、纸、墨、砚“文房四宝”的省称。纵观汉字发展历史,正因有其书写工具和载体作为物质依凭,才得以生生不息,世代传扬。汉字发展史,也是汉字书写工具和载体的演变史。
《易传·系辞下》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言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后不敷使用,圣人便发明书契文字。“书”“契”连用,正说明两者在成就人类早期文化符号时,相依相随,难断区分。
新石器时代,彩陶出现,实现了人类进化史上一次质的飞跃,而孕育汉字渊源的陶纹刻画,也让“书”“契”各自发轫:陶纹出自笔涂,刻画出自刀契。山东大汶口陶文,书写和契刻并存,足见其时笔已出现,只是极为简陋,或如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言:“以竹梃点漆而书”,即用小竹棍蘸漆料以书写。时过境迁,大量原始社会的陶器刻符仍留存至今,无不展示着史前中华文明遗迹的成形主要以刀锥为笔,以陶面为纸。近年来,二里头文化考古新发现为汉字起源研究引入了源头活水。研究表明,其多样的象形符号与商代象形文字存在承继关系,而这些象形符号多刻画于陶器表面,进一步说明刀锥和陶器构成了汉字系统创制前期的“文房”。
殷商时期,汉字大量创制,用于书写的柔毫一直存在,但商王朝独特的卜筮需求让龟甲兽骨成了汉字的主要载体。在坚硬的甲骨上“钻凿陈卦”以“通神”,除了“书之”,更需“契之”。“笔”字初文为“聿”,甲骨文正像手持笔之形。“契”字《说文解字》作“栔”,“刻也”,以“丯、刀、木”会意,“丯”为刻痕,“刀”为刻具,“木”为契刻材料,载体虽有不同,但成形方式未变。
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建立,礼乐文化大兴,经久耐用的青铜器具成了汉字的主要载体。铜器铭文的成形,范铸为主,刀刻为辅,而对于范铸所用之泥模,也非刀具不可成。“则”字金文从“刀”从“鼎”,为会意字,“刀”为铭刻工具,“鼎”为铜器代表,显然其造字意图是以刻铭铜器为“法则”,这种“法则”的内涵或许较为丰富,但应包含着成就泥范时对文字视觉形态美化的刻削刮磨,仍然未离开刀具的参与。
甲骨也好,青铜也罢,都带有浓厚的权力地位象征。春秋以降,汉字的日常书写需求迅猛增加,促使同样的“刀笔”工具,开拓出了更加广阔的“契刻”天地:石玉、砖陶、碑碣、摩崖、玺印、货币,材质多种多样,形态各不相同,但汉字的成形仍然是“刀笔”的杰作。别具一格的“文房”内涵,成就了早期汉字的形态体势,也开启了汉字发展与“文房”演变密切呼应的时代风貌。
东周时代,完全撇开毛笔的刻画性金文出现,让毛笔书写文字的情形日渐衰微。但值得庆幸的是,毛笔被一步步逼出宫廷御用书写场合的同时,却在民间日常应用中觅到了更加广阔的用武天地。从玉石到简帛,从契约到典籍,毛笔在汉字书写中的权威地位渐渐得以确立。
据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载,蒙恬始作秦笔,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以羊毛为被,谓之“苍毫”。今天,素有“妙笔之乡”之称的河南项城孙店镇仍然流传着蒙恬拔兔毛制笔以传令的民间传说。然而,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墓发掘出一支保存完整的毛笔,笔杆长18.5厘米,一头剖为四片,夹兔毫于其中,以麻丝缠束,其形制与今日毛笔近似,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毛笔实物。
毛笔的大量使用,使其需要寻求与之匹配的载体,于是,取材方便,容易整治的简牍成了最佳选择。简牍作为汉字载体,应不会晚于商代。《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册”字作两条绳索将数条竹木简片编连成册形;“典”字从廾、从册,表示双手捧握简册。简牍的大量使用,实现了汉字的书写自由,也大大提升了汉字的书写速度。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正是得益于简牍的广泛使用。近些年来,大量战国楚地竹简文献出土刊布BOB半岛,有力地证明至迟在战国时代,简牍已然成了最为重要的汉字载体。毛笔和简牍成为“文房”的核心内涵,让汉字的成形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时代BOB半岛。不过,简牍易燃、易裂,搬运不便,空间有限,作为汉字载体,仍受到诸多实践性制约。相传,秦帝日批公文百廿斤,是为真实写照。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技文化日新月异,新的文字载体纸张呼之欲出。
纸张的出现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场革命,它比此前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文字载体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先民就尝试用各种材料制成了所谓的絮纸、麻纸。到了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纸张作为价廉实用的载体,很快得到普及应用,简牍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往后,历朝历代的造纸技术愈发精进,给汉字书写与文化传播带来了革命性进化,“文房”的真正内涵也得以实现。唐宋时期,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继发明,解放了汉字抄写的桎梏,汉字与历史文化的传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增强。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一时抄写经书盛行,西方书写工具东渐。至唐代,吐蕃人将竹笔带入西域,汉民族也开始使用硬笔进行汉字书写,但使用范围有限。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密切,融入科技元素的硬笔传入我国。1928年,上海自来水笔厂创建,国产钢笔开始批量生产,钢笔的使用逐渐普及。随后,铅笔、圆珠笔等书写工具也在我国开始使用并迅速发展普及,汉字书写迎来了硬笔时代。
步入信息化社会,电报BOB半岛、电话、电视等相继发明和应用,让文化信息得以通过语音、图像来储存和传播;特别是伴随电子信息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汉字载体的成员增添了磁盘、光盘等虚拟数字化介质,使得汉字的成形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的编码、解码而轻松实现,也能够在纸、碑、石等传统载体和电子屏幕等数字化载体之间自由转换。汉字的书写工具和载体迈入了全新发展时代。
正如有学者所言:“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继造纸术、印刷术、打字机之后第四次伟大的文化工具的革命。古老的方块式汉字终于适应了这场革命,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科学技术推动“文房”的内涵发生着巨大变化,“文房”反哺了汉字的多元化成形。
纵观“文房”的前世今生,书写工具“刀笔”在陶碣、甲骨、钟鼎等坚硬载体的次第实践中走向了衰微;“软笔”在简帛向纸张划时代的演进中异军突起;近代以来,“硬笔”与纸张“切磋磨合”的同时,科技元素的介入让书写工具和载体走向了多元。但不论如何,书写工具与载体相依相存,相互成就。书写工具迭代更替,总会在与时俱进中适应最佳的承载客体;载体移时变革,一直在物竞天择中契合独特的书写工具。
时至今日,汉字信息的交流与传播几乎离不开数字化介质,承载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古老汉字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使得汉字文明的魅力与光彩更为耀眼。